医事法学5岁心肌炎患儿入院9小时死亡,
2016-12-25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动动您的小手
点点右上角的按钮,分享到朋友圈
作者: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陈国祥姚麟宋儒亮官健许雯
病例简介
患儿男,5岁,因“发热2天,频繁呕吐1天”于年8月8日12时50分到A医院急诊科就诊,值班医生诊断为急性胃肠炎,给予头孢他啶抗感染及输液等处理。当天下午4时许,在输液过程中,患儿再次出现频繁呕吐、脱水,医生在复诊后,将患儿转入该院儿科病房。患儿于当天18时带液入住儿科病房。入院查体:体温36.2℃,脉率次/分,呼吸频率24次/分,神志清,呼吸平顺,精神疲倦,对答切题,颈软无抵抗感,双侧瞳孔等圆等大,对光反射存在。咽部充血,双侧扁桃体Ⅰ度肿大,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音,心音稍低钝,腹平、软,肠鸣音减弱。入院诊断:发热、呕吐原因待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急性胃炎?);中度脱水。医生给予抗感染,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治疗,但患儿病情仍持续恶化。20时30分,患儿出现烦躁,医生给予药物镇静处理。20时55分,患儿再次出现烦躁,牙关紧闭。21时,患儿呼吸、心搏骤停,全身发绀。医生及护士立即对患儿实施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球囊面罩加压给氧、使用肾上腺素、心电监护、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等一系列抢救措施,但患儿一直未能恢复心跳、呼吸。抢救持续至22时20分,患儿心跳、呼吸停止,双侧瞳孔散大,心电图波形为一直线,医生向家属宣布患儿临床死亡。
原告(患儿家属)
患儿在A医院急诊科输液过程中,原告发现患儿烦躁不安,上身出汗严重,手脚冰凉。原告找到医生反映病情,要求及时进行处理。但医生认为患儿上述症状是急性胃肠炎的正常反应,没有过来察看患儿的病情,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处理。
当天下午约4时,患儿病情加重,呕吐更加频繁,并出现烦躁不安、出汗严重、手脚冰凉等病情,原告要求医生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医生这才将患儿转入住院部。
转入住院部后,患儿病情再次加重,原告再次向医生反映患儿病情,要求医生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医生对原告说,根据化验结果,患儿水、电解质紊乱,要补钾、输液。在输液过程中,患儿病情急剧恶化,最终死亡。
从患儿到A医院急诊科就诊,到按被告的指示住院治疗,时间长达8~9个小时,被告连患儿的血压都没有测量,被告的不负责任可见一斑。
据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共计10万元。
被告(A医院)
原告对事实的陈述不正确。患儿在急诊科输液过程中,原告来反映患儿病情的时间是在当天下午4时后,接到其反映后,我院急诊科医生立即复诊,并将患儿转入儿科病房。
儿科医生给予抗感染、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等对症支持治疗,并完善相关检查。
当天20时30分,患儿出现烦躁,医生给予药物镇静。患儿于20时55分再次出现烦躁,并随即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医务人员立即对患儿实施了一系列抢救措施,但患儿一直未能恢复心跳、呼吸。22时20分,患儿心跳、呼吸停止,最终死亡。根据法医病理尸检的死因鉴定结果(表1),患儿死亡是由自身严重疾病所致。
综上所述,我院对患儿的整个诊疗过程符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我院对患儿的整个诊疗过程与患儿死亡的结果既不存在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医疗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依据法定程序先后委托某市医学会、某省医学会对本病例进行鉴定(表2和3),两级鉴定机构分别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均认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虽然两级医学会对患儿病因的表述略为不同(某市医学会认为是“病毒性心肌炎”,而某省医学会认为是“暴发性心肌炎”),但均认为患儿因该病进展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多系统器官衰竭而导致死亡,并且由于该病起病急骤,发展迅速,病情凶险,死亡率高,早期诊断常有困难,导致难以早期采取有效救治措施。因此,被告在诊疗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过失,也未能及时确诊病因,但被告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患儿死亡无因果关系。
被告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行为,故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因此,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是否存在怠于履行职责的问题,因被告予以否认,而原告又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确认
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于原、被告双方均未在限期内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因此,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为生效判决。
各方意见
医方代表:医师姚麟
医院胜诉告终,但医院医疗安全管理中仍有经验、教训值得吸取。比如,虽然暴发性心肌炎早期诊断常有困难,难以早期采取针对性强的有效救治措施,但本案是因未考虑到此类儿科急症,对该患儿病情的严重性评估不足,未能及时将患儿病情的风险告知家属而引起。即使在后期医师两次下病重通知,家属对患儿病情的严重性仍认识不足,对不良预后没有心理准备。关于医生是否存在怠于履行职责问题,医院提供了医生诊疗经过情况下,原告认为医生怠于履行职责的主张要举证证明,否则法院不予确认。
律师代表:律师陈国翔
省、市医学会的两次鉴定结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就本案而言,医方不存在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医疗行为是无须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前提。患儿的死亡是其病情发展的结果,与医疗过失无关,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与患儿的死亡无因果关系。在原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请是正确的。
法官代表:法官官健
本案经两级医学会鉴定,不管是市医学会所表述的“不足”,还是省医学会所认定的“过失”,都说明医方对于患儿病情的严重性缺乏认识,观察病情不够全面、仔细,甚至没有测量血压,反映出重视程度不够,处理经验不足。这足以认定医方没有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在法律上已经构成过失。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该医疗过失行为与患儿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是决定医方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关键。诚如医学会鉴定中所言,早期诊断常有困难,导致难以早期采取针对性强的有效救治措施,但这并不等于一旦患了该病,就相当于判了死刑。恰恰相反,如果医方能采取及时、正确的诊疗措施,患儿并非没有生还希望。
在法律界,对于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判断标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本思想是“一个可能性的判断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根据社会一般见解,能够确定加害行为客观上有可能导致损害后果,就可以认定二者具有因果关系,并不要求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强调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本案而言,医方的过失行为减少了患儿可能成功获救的机会,与患儿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当然,比较原发病因素与医疗过失因素对患儿死亡的原因力大小,原发病显然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因此医方的责任程度并不大,可能占10%~20%比较合适。
本案启示:临床医疗是医学与法学有机结合的活动
广东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宋儒亮
一直以来,人们都对“知情同意书是不是霸王条款”存有质疑,这表明,患方对医方想做的事情并不是都能表示认同和理解的,患方、医方总是认为官方未充分保护本方的利益。
如何避免诸如医生留泪而患者死亡等双输案例再发生,如何做到依法行医并防范出现不利医疗纠纷后果,值得各方深思,特别是医方更需从法律意义上更好地了解、认同当下进行的各种临床医疗。
紧急类临床医疗
结合临床实践,从法律角度,可将临床医疗大致分为常规类、紧急类和实验类三大类,本病例属于紧急类临床医疗。从法规角度,紧急类临床医疗包括但不限于:急危患者(《执业医师法》)、危重患者(《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生命垂危患者(《侵权责任法》)、急危患者/垂危患者(《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垂危患者(《护士条例》等。
结合医疗损害的司法实务,开展紧急类临床医疗的关键是“可签知情同意书”;司法实务的争议焦点主要是:是否紧急(考医生)、应否签字(考患者)、是否批准(考领导)和能否过关(考法院),难点是“知情但不同意而存争议”。
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出台,紧急类临床医疗的要求发生了一些变化。《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紧急情况是必须救”,医院、医生都有明确要求。对医院是不救就转,不转就救。《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患者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患者,应当及时转诊。”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对医生则是必须要救治,比如《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
《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紧急情况是可救可不救”,紧急情况下救不救关键在院长,医院有了新要求,比如《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结合医疗损害的司法实务,考察当前紧急类临床医疗现况,存在这样一个判断:救有风险而不救有危险。因此,两弊权衡取其轻而不是利弊权衡是价值判断的关键,也即救还是不救,既考验医疗水平,更考察法律权威。
医与法的有机结合
第一,依法行医要落到临床医疗活动之中,它不是临床医疗之外的事情和工作。依法行医既是医疗救治、医疗管理的需要,也是医疗法治的要求。
其次,懂法行医才能赢纠纷,才能防范违法甚至犯罪发生。从行政监管角度,截至年10月,我国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有11部,行政法规39部,部门规章部。从很大意义上说,能否保护好医方合法权益、能否监管好临床活动、能否预防好医疗纠纷,这些法规的履行非常关键。例如,有医生对超过登记范围以外患者不救治,理由是担心构成非法行医。因此,要合法行医,就不能在火车上、公路边、车站旁救治患者,但法规规定并非如此。面对急诊和急救,医疗机构的诊疗活动是可以不受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限制的,而且受法律保护。
第三,就临床医疗活动而言,满足法律要求是工作的底线。应当按照《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在清楚医方说明内容和患方签字要求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正确区分三类临床医疗的法律性质,不能一概而论。患病就诊是诉求,知情同意是需求,依法行医是要求。医疗的目的是保护生命健康,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权,而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法对人权的价值犹如医对生命的意义,医法结合就是生命保护和人权保障二者的有机融合。离开医的治疗是谋财害命,离开法的医疗是草菅人命,因此,临床医疗是医与法有机结合的活动。
不为哗众取宠,只为见证医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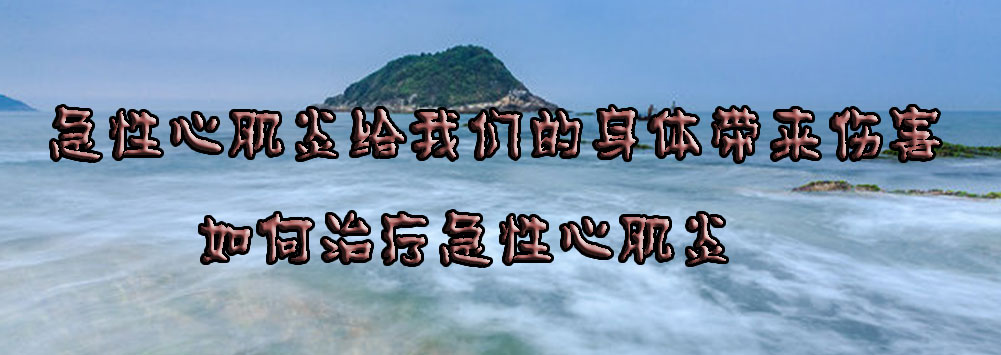
 健康热线:
健康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