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河人家
2021-7-2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阎河人家
文/柳长青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阎家河镇是麻城市的千年古镇。这里曾是古麻城的县治所在地,因唐代洪州都督阎伯屿居住于此而得名。今天的人们习惯称她为阎河。经过连续多年的脱贫攻坚,这里的贫困发生率从年的20.74%下降到0.%。截至年9月,全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户人,已有户人成功脱贫。尚未脱贫的7户17人也有望在年底实现脱贫。为了见证脱贫攻坚的成效,中秋节前,我特意走访了几户阎河人家。
刘世卫家的奖状墙刘世卫是麻城市阎家河镇阎家河村六组村民。时隔一年,我们再次相见时,他正在新建的楼房整理院落,为乔迁作最后的准备。
怎么不声不响就盖起一座楼房来了?刘世卫放下手里的铁锹,灿然一笑,十分开心地说,这房子是去年就开建的,慢慢修整,直到现在才基本完工。同行的村支书说,好多粉刷都是他自己做的。刘世卫介绍,房子上下两层,有个平方,总共花了30万元。因为建房的面积大,加之又是楼房,所以不能享受危房改造的政策补助。建造新楼房无疑是脱贫的显著标志,但这30万从何而来,会不会因为新建一座楼房,又返回贫困?我不无疑惑地问。刘世卫说,所花30万的大头是找开废品回收公司的舅哥借的,还有七八万,是这两年跑运输和妻子打工赚来的。
刘世卫的新楼房宽敞明亮,里面空空的。我执意要到他的老屋去看看。在那里能够让人生出对这个中年男人无比的钦佩。同时,我也想让同行的人一起去见识一下他家的墙壁。
刘世卫的老屋离新楼房只有多米,这也是一座两层的楼房。只是这座年建造的老楼,自从建成就一直没有进行过外装修,只把堂屋的墙壁进行过简单的粉刷,用水泥打了地坪。外墙的红砖都裸露着,有的发黑,有的长满了青苔。刘世卫说外墙和屋顶渗水多年了。虽然如此,屋内的地面干净整洁,桌椅等家什收捡得整齐有序,初来乍到的人,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大男人收拾的局面。
我到他这老屋来过三次,每次都没见到女主人。这一次才问清,20年前,她就经熟人介绍,到厦门的一家家私厂去打工了。只是4年3月,一对双胞胎儿女出生后,她的打工生涯才有过一两年的暂时中断。对此,我进行过反复的核实和推敲,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0年,他们的女儿才3岁。离开丈夫,抛下幼小的女儿,只身南下,打工挣钱,这得下多大的决心?这又该是多么的狠心?可事实就是如此,妻子出去打工了,而刘世卫则留在家里。除了种好2.16亩承包地,更主要的工作是在附近跑短途货运,因为他熟悉的业务都在这四里八乡。这时候,虽然有爷爷奶奶搭把手,但刘世卫仍然还要既当爹又当妈,料理家务,照看孩子。
能够证明他既当爹又当妈当得还不错的,是他的三个孩子每一年、每个学期都要为他拿几张奖状回来,而且从未间断。他大女儿的奖状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拿到现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有这个出生于年的女孩有奖状拿回来。在她进入初中后,这种一花独放的局面被打破,她的一对双胞胎弟妹也能从幼儿园拿几张含金量高的奖状回来。后来,姐姐上高中、双胞胎弟妹上小学,姐姐上大学、双胞胎弟妹上初中,如今姐姐读研究生,双胞胎弟妹读高二。他们相互比拼着,拿回了一张又一张奖状,慢慢贴满了两面墙壁。
大女儿的奖状有的已经退色发黄,但数量仍然远远领先于她的双胞胎弟妹中的任何一个。这个堪称“学霸”的女孩,从西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后,于年直接考上了清华大学的法学研究生。由于姐姐做出了榜样,她的一对双胞胎弟妹的学习也很用功,成绩也很不错。只是刘世卫还有那么一点遗憾,虽然这对双胞胎都在读高二,但儿子却没有与妹妹一同进入麻城一中,尽管儿子在麻城三中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麻城一中是黄冈有名的重点高中,进入该校的学生只要不出什么意外,考一个重点大学,基本不在话下。在三中的儿子再努力冲一把,赶上妹妹也不是没有可能。按现在的趋势,将来考个好大学根本不成问题。我对镇村干部说,要是将来这对龙凤胎一同考进同一所名牌大学,那必将是轰动阎河、轰动麻城、轰动黄冈的特大新闻。刘世卫一家能够为国家培养出三个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值得天下的父母羡慕和敬佩。刘世卫只是淡淡一笑,却洋溢出无比的自豪和自信。现在,他的新楼房已经落成,搬进去是迟早的事。我问,搬进新楼后,这老屋会拆吗?他说,不拆。我说,那你一定要把这些奖状保存好。他说,要得。我又说,这是你的儿女刻苦努力的见证,也是你和妻子的骄傲,你真的要保存好。
刘世卫的日子,随着儿女们奖状的日益增多,平安过到了年。年初的一场大雪,如期而至,覆盖了远山近岭和大大小小的村庄。货运跑不成了,刘世卫就趁着下雪在家歇息,正好他这几天感到有些不舒服。原以为歇两天就会好的,医院。可在家歇着歇着,人却突然晕倒了。幸亏有父母过来看他,医院,一查,是爆发性心肌炎,麻城诊治不了,医院。这个病好凶险,几天的功夫,就花费了18万多。这一下,不仅把几年的积攒都用完了,还借了一大笔债。这一年,他18岁的大女儿,正好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已经11岁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也在上小学五年级。就这样,通过精准识别,他在这一年成了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在确定为贫困户后,医药费报销了10多万元。大女儿上大学,申请到了每年元的助学贷款。一对双胞胎也获得了每人每年多元的国家助学金,虽然三个孩子的生活费和其他方面的开销,还要靠他们夫妇来提供,但大的问题已经解决。出院以后,刘世卫需要休养,不能干重体力活,而且每半年还得做心脏彩超检查一次,村里就给他提供轻微劳动的公益岗位,还为他申办了4万元小额信贷,第一次入股分红就拿到了4千元。到年,他感觉身体好多了,就自筹2万元,买了一台二手车,重新跑货运,当年就把买车的钱给赚回来了。在干活挣钱的同时,继续担负起既当爹又当妈的职责使命。给他回报的仍然是孩子们继续拿回家的那一张张奖状。
细看贴满两面墙壁的奖状,我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我对一同前来的同志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刘世卫和他的妻子都发一张大大的奖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确实应该!其实,眼前这一张张奖状的背后,正隐藏着他们夫妻应得的那张奖状。
刘世卫的妻子在外打工,每年只回来过个年,前后待上十天半月就又去了厦门。我问为什么一年当中不让妻子多回来几次?刘世卫说,路太远了,来去得好几天,光路费就要花一千多。我问,你去看过她吗?他摇摇头。为什么不去看她?忙啊,再说还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要人照看哩。说忙最不是理由,舍不得花那一千多元的路费才是关键。
我又问,那您欠不欠老婆?这个年仅49岁,看上去很壮实的汉子,嘿嘿一笑,竟憋着普通话,提高嗓门说,那有个什么欠头呢?!也许是我的问话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最大痛点,他才用矢口否认来加以掩饰。陈毅元帅曾有诗云: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表达他对妻子强烈的思念之情。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军事家,尚且有儿女情长的时候,作为一个正值壮年的凡夫俗子,难道他就没有思念妻子的人之常情?
我想,他是有的,只是他不愿说将出来。我说,忙的时候,可能不欠。如果闲来无事你也不欠?就像前几天一直下雨,独自一人,空守在家,夜静更深,冷雨敲窗,你也不欠她吗?他仍是嘿嘿地笑,避而不答。我说,你们夫妻常年分居两地,相距千里迢迢,真是相互为难,苦了自己。说到这里,我竟有些激动。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国家的现代化,有多少恩爱夫妻在两地分居,在牺牲他们个人的幸福啊!他说,那没办法,老大在读研究生,“一对双”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还得再打几年工。再说我们隔几天就要视频联系一次的。听闻此说我不禁为他高兴了一把,通过视频隔空相抱,聊解相思之苦,权当是夫妻梦里来相会吧。
我又问,她今年回来有多长时间?他说有三个多月。我说,那你要感谢疫情,不然你们夫妻哪能团聚这么长时间呢?他很坚决地说,不能感谢疫情。疫情对国家的影响太坏了,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来感谢疫情。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情怀和精神境界。难怪他的儿女们那样发愤图强,他们也都有这样的精神和情怀!
既然谈到了疫情,自然要问疫情对他跑运输有没有影响。他点点头,说有半年没跑了。我说,那这半年就没有收入了,会不会返贫?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不会,没跑运输,我还在做其他的事。一旁的村支书说,疫情期间,村里镇里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都很关照,站岗守卡,消毒消杀、打扫卫生,分发物资,都是安排贫困户来做的,一般一百块钱一天,说是一天,其实也没有几个小时。刘世卫说他疫情期间也搞了两千多块钱的收入。
我说,那你就是一个坚定的脱贫户了。刘世卫说,是坚定的脱贫户!说完又嘿嘿地笑了,笑得那么自信、自在、自如,笑得令人肃然起敬。
刘世成的合作社从刘世卫家出来,穿过几条小巷,我们突然被带进一家小超市。超市很冷清,一个年轻女子正和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在玩耍。几排货架间隔宽敞,上面的商品不是那么满满当当,却也称得上品种丰富。超市里散放着几张略显陈旧却依然坚实的小木椅。看得出,这既是家小超市,也是普通人家的堂屋。只是这堂屋的面积足有一百平米以上。
一个身材高挑,有些瘦削的中年男人闻声而出。他满面春风,一边热情招呼我们坐下,一边去货架上取瓶装的矿泉水给我们,看那麻利的动作,就觉得这人很大方。我们还没坐下,他的烟就递上来了,是黄鹤楼硬珍品的那种。推辞一番,我们拉起了家常。他说,他叫刘世成。怕我们听不清还逐字作了解释。家里有8口人。
父母都80多岁了,身体都还健朗。他和妻子都有五十六七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媳,两个孙子。儿子在外打工,儿媳妇家带小孙子,同时负责看店。老伴主要做些家务,照看老人。原来这是个四世同堂之家,感觉他好有福气。不禁又问有兄弟姐妹吗?刘世成说,上面有个姐姐,现在也在带孙子。下面有个弟弟,还有个妹妹。弟弟是跑运输的。妹妹家养了20多头牛,外甥也在跑运输。村支书说,他这一大家子,个个的日子都过得红火。真是你说的有福气。
见我们在说话,那年轻女子把正在玩耍的小孩抱走了。刘世成说这是小孙子,大孙子有5岁多,去上幼儿园了。我们又问他这超市的经营情况。刘世成说,超市开了20多年,但现在生意不好做,开小店开超市的人多了,都快要被挤死了,再加上现在的实体店都不景气,所以这个店没赚什么钱,只能顾一家人的生活开销。
听他这么介绍,我越发有些疑惑。前年,我第一次到阎河走访贫困户时,也到过一户利用自家堂屋开小商超的人家,当时满心疑惑,能够开小超市的家庭怎么会是贫困户?坐下来一了解,才知这户人家的两个小孩都得了脑瘫症,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专人照料。镇村两级帮她开这个店,就是为了让她在照料孩子的同时尽可能搞点收入,助她脱贫。可刘世成家不是这种情形呀。
我终于按捺不住,问他家被确定为贫困户是因为什么原因?刘世成说,我不是贫困户。我一听,不免心生责怪。因为来之前我反复交待过,一定要到真正的贫困户家去走访慰问,怎么把我带到不是贫困户的家庭来了呢?这倒不是我小气,舍不得刚刚送出的那盒月饼。见我半天没接话,同行的镇人大主席团范主席说,他是开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听这一说,我疑惑尽消,顿时来了兴趣。
于是切入正题,问他开办的是什么合作社。刘世成说,开了养殖合作社,主要是养猪养牛,另外还承包了一口十几亩的鱼塘。问养了多少猪,他说高峰时有多头,去年受非洲猪瘟影响,现在只存栏头。这些猪是请专人来饲养的吗?他说,请了四个贫困户轮流帮忙。也不是长年累月要人帮忙,只是忙的时候就打电话请他们过来,一次就来一个人,家里谁有空谁来。报酬是一天一百块。说是一天,实际只是两三个小时吧,这里忙完了,就去忙其他的事。那这些贫困户一年能拿多少工钱呢?
他说目前规模小,每户三四千吧。农村人说话爱说概数,说三四千其实就是四千。怎么不把规模扩大些?他说,主要是行情不好,特别是非洲猪瘟太坏事,去年就消杀了40多头,好在国家给了补贴。补贴标准是母猪一头补一千,大猪每头补元,小猪每头补元。那一头猪出栏能赚多少钱?他说,如果行情好,毛猪能有十八九块的价格,一头就能赚0元。养猪这一项一年能不能赚30万?他说那赚不到,就是一头赚0元,总共只有百把头猪嘛!我说,不是存栏有头吗?他笑呵呵地说,那也赚不到30万。
村支书介绍说,他是从开超市开始发家的。开超市赚了钱,就养猪,养猪赚了钱又养牛。当年读书的时候,他就爱跟在别人后面看养牛。农村人有个传统,叫做穷不丢猪。看人家养猪,他也想养。一开始就养了五六头母猪。慢慢地试,逐步做大了。当初给猪防疫连针都不会打,每回都要请人来帮忙。现在成了师傅,防疫的事都是自己做。
刘世成接着说,养牛是从年开始的,到今年有9年了。养的是黄牛,目前存栏40多头。当年在村部的农家书屋,看到了一本养牛的书,慢慢琢磨,觉得有点奔头,就试了下,一试也成功了,到现在就放不下手了。这使我想起早些年前“赶着黄牛奔小康”的说法,就问一头牛能净赚多少?他说四五千吧,养黄牛要隔年养,一般这个时候买小牛,等来年过年前卖牛。是圈养还是放养?他说养肉牛主要是圈养。要请人帮忙吗?他说是的,主要是铲牛粪出栏,再就是割草,要请人。问请了多少人,从哪里请的人,怎么给报酬。他说,还是那4户人家,报酬跟养猪差不多,一年下来,四五千吧。村支书说,这个不能瞒他的情,一个贫困户一年少说也能从他这里拿个万把块钱。
带动的贫困户是自己找的还是村里安排的?刘世成说,他是这个组的组长,要用人的时候跟村里说了,由村里介绍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这些人的劳动态度怎么样?他说,都没得话说。这些人家没脱贫不是因为好吃懒做,主要是有小孩读书,再就是得了大病。现在只要肯做事肯出力,做个小工一天也能赚一两百元。在我这里做事劳动强度不轻不重,比干农活还轻松一些,就是气味重一些,喂牛的时间稍长一些,喂猪一般只要一两个小时就能做完。我问他与这几户人家的关系怎么样?他说蛮好的。村支书说,他们的关系很融洽,像兄弟伙的一样,随叫随到,都是当作自家的事在做。这几户脱贫没有?还会不会返贫?村支书说,都脱贫了,再不会又变成贫困户。他们除了在他这里获得一些收入,还有承包土地,还能到别处做事赚钱。我说,能去这几家看看吗?村支书说,随时都可以。
我突然记起来,他还有十几亩鱼塘。养鱼也请人帮忙了吗?刘世成说,鱼塘主要是自己打理,没有请人。我有些不相信,十多亩鱼池再怎么样也是得有一两个人才照看得过来的。刘世成说,鱼池是村里做工作要我承包的,现在讲环保,不准投肥,只能人放天养,所以用不着请人。
我们称赞他勤劳,肯钻研,自己致富了,不忘带动贫困户脱贫,很不简单。他说,都是靠政策好,像现在政策对养殖还是蛮倾斜,蛮好的。我问合作社带动了贫困户脱贫,镇里村里对他有什么扶持?他说现在找银行贷款好借,只是他这周转只要几个月资金就出来了,他希望能够给他提供几个月就还本付息的那种短期贷款。别人是想借借不来钱,而他则是嫌借钱的周期太长。看来这是个精打细算的人。
我们约定,再找时间,专门去看他带动的脱贫户。
香飘林家岗当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通村公路,进入林家岗村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芳香,而且愈来愈浓烈。同行的年轻人,一个说谁家的瓜子炒得这么香,一个说这是柴火灶上炒花生的味道。只有我知道,这是从榨油厂传出的香味。及至我们在靠近路边的一处平房前停下车来,我竟突然间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我儿时见过的榨油厂何似这般矮小?那用铁环和稻草包裹着的料饼一层层码得有两三人高,一二十个榨工要站在高高的榨台上,喊着号子,朝着一个方向,把那根竖得高高的、比碗口还粗的螺杆慢慢板拧下去。就眼前这点高度,说不定还真是个炒瓜子的地方,因为此前我听说过,有好多地方在大面积种植瓜蒌,瓜蒌籽不是要炒熟才能吃的么?
在此等候的驻村工作队长和村支书,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去,我才发现这就是一个简陋的榨油作坊。已是中午时分,里面的男女人等正忙碌着。他们有的在用筛选机除杂,有的在用剥壳机剥壳,有的在用转炉翻炒花生,还有几个人似乎是在排队等候。一台立式的榨油机正将炒熟的花生进行机械挤压,出油口正汨汨流淌着清纯透亮的液体。一位同行的年轻人,惊呼,哇,这就是5S压榨花生油吧?旁边的人不置可否,我也不知该怎么回答,捡起一块落在箩筐中的薄薄的状如小饼的饼粕掂量着,它正散发着热量和花生特有的清香。说实话,这样的全机械化的榨油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它跟我记忆中的榨油厂大相径庭。
驻村工作队长和村支书带我们参观完全过程,并作了详细的介绍。经过攀谈,得知驻村工作队长姓熊,是麻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村支书姓林。我更关心的是这里的真正主人或者实际负责人是谁。熊队长指着刚到转炉边查看炒料色泽的一位身材高大中年男子说,这个作坊是他们两口子开的。只顾忙乎的两口子也没说什么,我们相互点点头就算是彼此致意了。我注意到,自进屋来,这位中年汉子在每台正在运转的机器旁边都站立过一阵子,而且神情是那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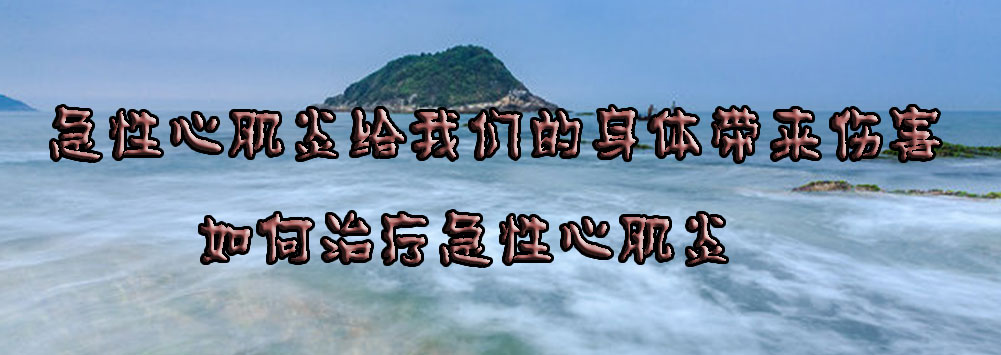
 健康热线:
健康热线: